文/阿潑(本文作者為記協執委,代表記協參加國際記者聯盟亞太地區記者會議暨工會聯合會議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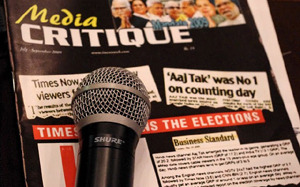 在我和大學同學畢業沒兩年時,一起去看了《那山那人那狗》,其中有一段讓我感傷,讓我同學淚流不止:一個深山裡的少年因讀書不易,只好函授讀大學,他盼著郵差為他帶來錄取通知單,郵差問他想讀什麼,他說「新聞系」,因為他希望記者來採訪他,但沒有任何一個記者來,所以他想讀新聞系,好自己採訪自己。
在我和大學同學畢業沒兩年時,一起去看了《那山那人那狗》,其中有一段讓我感傷,讓我同學淚流不止:一個深山裡的少年因讀書不易,只好函授讀大學,他盼著郵差為他帶來錄取通知單,郵差問他想讀什麼,他說「新聞系」,因為他希望記者來採訪他,但沒有任何一個記者來,所以他想讀新聞系,好自己採訪自己。
對新聞懷有夢想的我們,踏入職場沒多久,面對真實的媒體環境,總覺得被澆了好多冷水,一下子就感到灰心了。深山裡少年的話,竟然啟動了我們的傷心,哭得不能自己。我想身邊的觀眾一定好奇,這兩個丫頭怎麼哭了?
想起這件往事,是因為採訪了英國《衛報》的亞洲環境特派員Jonathan Watts,並且讀了他寫的書。
採訪前,他在天下雜誌的晚宴上展現他拍的照片說:「你們絕對都不會想到這些地方去。」我看了一下現場的企業家們,在心裡點點頭。我又看到一篇關於他的報導上說:
正如大多數新聞記者一樣,我們每天要閱讀中國的報紙,與這裡的記者、NGO組織建立良好的關係和資訊管道。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,你得確定自己能到現場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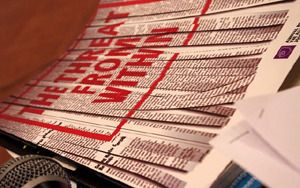 那天的採訪是個非常愉快的經驗,我們還聊到了胡佳。本來我準備了一個問題問他,但因時間不夠加上他的回答讓我放棄了這個問題:「作為一個啟動工業革命造成環境破壞連鎖反應的西方國家公民,會不會遇到許多「抵抗西方觀點」的人或問題,你知道,特別在中國。」Watts的確是個好記者,他有自己的態度、動機和想法,然而他非常理性,不把問題往一個地方推,事實上他也不會去指責是誰的錯或誰造成的,或者他只要批評中國政府就行。但我們都知道那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問題。
那天的採訪是個非常愉快的經驗,我們還聊到了胡佳。本來我準備了一個問題問他,但因時間不夠加上他的回答讓我放棄了這個問題:「作為一個啟動工業革命造成環境破壞連鎖反應的西方國家公民,會不會遇到許多「抵抗西方觀點」的人或問題,你知道,特別在中國。」Watts的確是個好記者,他有自己的態度、動機和想法,然而他非常理性,不把問題往一個地方推,事實上他也不會去指責是誰的錯或誰造成的,或者他只要批評中國政府就行。但我們都知道那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問題。
訪問中,他時而跟我說:「你也是記者,你應當了解......。」是的,我是記者,但正因為我是記者,我才比其他人有機會聽到他的想法和故事,尤其他如何去當一個記者。當晚我留言給他,謝謝他inspire了我。
走出咖啡店,想起了《那山那人那狗》以及那晚看電影時同學的淚水。因為我便走在當時工作的區域及當時看那場電影的電影院附近。
 為了「轉換頻道」,做個break,採訪完後,邊吃飯邊看壹週刊。竟看到張翠蓉專訪(話說,前陣子收到他寄給我的信讓我頗驚喜),內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,但他說了一個例子讓我鼻酸。
為了「轉換頻道」,做個break,採訪完後,邊吃飯邊看壹週刊。竟看到張翠蓉專訪(話說,前陣子收到他寄給我的信讓我頗驚喜),內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,但他說了一個例子讓我鼻酸。
張翠蓉說,在他懷疑自己的工作時,遇到一個阿富汗喀布爾大學的新聞系學生,於是問這個學生:「為什麼要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讀新聞系?」這個十九歲的年輕人回答:「我沒有辦法想像一個沒有記者的社會會如何。」這段對話讓張翠蓉開始振作起來。
我想起前陣子到峇里島參加IFJ (國際記者聯盟)亞太地區記者會議(暨工會聯合會議)時的經驗。
還沒開會前,我和香港記者就先聊開了,爭著批評自己國家(?)的媒體環境有多糟,會議開始暖身時,因工會(UNI)的加入,所以很多倡議的討論都在勞動條件保障、工資等等,等到隨機分取的小組會議開始,我屬於「討論工作安全(safety job)的哪組,由於到峇里之前,我才在台灣記協群組「靠么」說:電視台記者在颱風天這樣工作主管到底有沒良心啊,記者命是有這麼賤嗎之類的。而香港記者此行和我談到這個也有所感,他們也是有八號風球掛起記者要到前線「走秀」的問題,所以我的對這個議題的定義和心理準備是這樣的,台灣新聞台記者天災前安全不保云云(我覺得談會不會隨時被炒魷魚這種safety太low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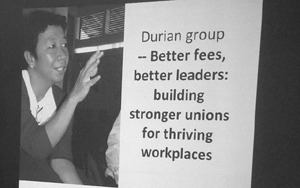 不料,真的不料,我那一組的記者分別來自於柬埔寨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和阿富汗,當IFJ工作人員才說第一句話:「怎麼定義safety job。」阿富汗記者就先說話了:「大家關心的問題或許是如何保住工作和工資,但對我們來說,怎麼保住生命不被殺害才是重要的問題。」一句話就讓大家沉默。面對動不動被殺害的記者,我是要怎麼把台灣的颱風秀說出口(在心裡吶喊~~~),還好馬來西亞印度裔記者追進,繼續follow這件事說記者不能靠別人保護,「自我保護」這件事該被訓練等等,而後柬埔寨記者很上道以菲律賓記者被大屠殺的事情繼續發展討論,於是我們這組的討論主題變成:「為了不死。」(這是我掰的,但我心裡的確是這樣想)作為其中一個稍微進步、所謂有新聞自由的國家的記者,我心中os超多。
不料,真的不料,我那一組的記者分別來自於柬埔寨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和阿富汗,當IFJ工作人員才說第一句話:「怎麼定義safety job。」阿富汗記者就先說話了:「大家關心的問題或許是如何保住工作和工資,但對我們來說,怎麼保住生命不被殺害才是重要的問題。」一句話就讓大家沉默。面對動不動被殺害的記者,我是要怎麼把台灣的颱風秀說出口(在心裡吶喊~~~),還好馬來西亞印度裔記者追進,繼續follow這件事說記者不能靠別人保護,「自我保護」這件事該被訓練等等,而後柬埔寨記者很上道以菲律賓記者被大屠殺的事情繼續發展討論,於是我們這組的討論主題變成:「為了不死。」(這是我掰的,但我心裡的確是這樣想)作為其中一個稍微進步、所謂有新聞自由的國家的記者,我心中os超多。
儘管在行前,余佳璋大哥已經跟我大略解說一下亞太地區媒體情勢等等,所以我也知道菲律賓大屠殺事件,不過,真的放在眼前討論,真的還是讓我覺得很難以置信又痛苦又有種莫名的感覺。我曾跟另一個專跑中國維權事件的香港記者討論到,在中國跑新聞,比起如何保護自己,我們似乎都需要「被訓練」如何保護我們的受訪者,我們自覺這討論起來有些殘酷和悲壯,但怎麼樣都比不上連保護自己都沒辦法的狀況。
總之,光那個討論就讓我像是個來自城市鄉巴佬。
 後來幾天的討論是根據區域,東亞和紐澳的一組,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他們一組,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等一組。我當然和日韓香港紐澳記者一組,討論outsource、工資啪啦啪啦的問題,可是我總不能專心,而且,我們和香港根本沒工會,韓國很強但也很辛苦,而日本根本就是「派遣文化」了,紐澳我其實不想管(XD)。但我人在曹營心在漢,老是想著別組的討論如何如何,我跟香港記者說:「他們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啊。」
後來幾天的討論是根據區域,東亞和紐澳的一組,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他們一組,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等一組。我當然和日韓香港紐澳記者一組,討論outsource、工資啪啦啪啦的問題,可是我總不能專心,而且,我們和香港根本沒工會,韓國很強但也很辛苦,而日本根本就是「派遣文化」了,紐澳我其實不想管(XD)。但我人在曹營心在漢,老是想著別組的討論如何如何,我跟香港記者說:「他們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啊。」
那幾天,只要有機會和其他地區記者聊天,如阿富汗、東帝汶、巴基斯坦、尼泊爾、印度、柬埔寨......我都會問一件事:「在你們國家,記者是一個好的工作嗎?」
會問這個,是因為我自覺在台灣這個職業不被尊重,韓國記者也這麼跟我說他們國家的情況,香港記者也同意。所以我對這些跑新聞容易招致危險的國家感到好奇。出乎我意料的,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:因為薪水好,人們需要我們。「但你們的工作很危險。」我都會這樣回答,他們說:「可是值得。」
如同阿富汗的新聞系學生說的。
(BTW,訓練他們的常是歐美的記者,但「代替」他們發聲的,也都是西方記者,而不是他們自己。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記者跟我說,對,他們也不喜歡CNN觀點,但他們是為了自己的人民工作,他們的同胞需要知道對他們有用的新聞,不是那些苦情的悲慘的被破壞的一面,這是他們的工作。CNN無法取代他們。)
 <--左起分別為馬爾地夫記者、柬埔寨記者、馬來西亞記者、阿富汗記者和巴基斯坦記者。
<--左起分別為馬爾地夫記者、柬埔寨記者、馬來西亞記者、阿富汗記者和巴基斯坦記者。
那幾天的討論跟經驗讓我百感交集,難以筆墨形容,不過我深刻體悟一件事,除了自己,沒有人可以幫你解決你的問題。當我對於無法協助阿富汗記者而感到失望生氣時,突然也了解到我們置入性行銷的問題也無法被他們幫助。作為記者,我們只能相互理解和聲援,繼續為了新聞自由和品質而奮鬥。(聽起來很熱血,但現實就是為自己的無力找藉口,我一點也不想說,我最大的心得是為自己慶幸,工作不需要考慮到生命安全。只是閒聊時,我開玩笑我們和香港記者的死亡率來自於過勞死,而一次和韓國記者喝咖啡時,不知為何他突然天外飛來一句:「我們國家的記者應該都是喝死的。」他說,下班拼酒是韓國記者的文化了)
有一幕倒讓我感動很久,一個菲律賓記者報告時,主動提起香港巴士劫持事件,香港記者回以評論(忘了確切內容)。到了最後一天,要確認共同聲明時,香港記者站起來為菲律賓的新聞環境爭取更多的注意和呼籲。我忍不住跟香港記者說:「我好感動喔。這算是一種大和解嗎?」香港記者回我:「要不是這個事件,我們都不會曉得菲律賓這麼糟糕,可憐的是他們的人民和記者。」
p.s 該記者和我一樣都是因為受到六四影響而立志當記者的。









0 意見:
張貼留言